z6尊龙凯时官网程正民(1937—2024),福建厦门人。195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在文艺理论组任教,讲授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调至苏联文学研究所,曾任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1993年调回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曾任中文系系主任。著有《20世纪俄苏文论》《金的诗学》《俄罗斯文学新视角》等。
2月20日早上八点多,当程正民老师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时,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那天下午就有新学期的第一次课,我得有所准备,但备课期间不断走神,有关程老师的点点滴滴蜂拥而来……
我知道程老师的名字是1993年,但见到他本人已是1999年。那一年,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在童庆炳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童老师打头阵,给我们开设了《文心雕龙》专题课;程老师则紧随其后,与另一位教授合开一门西方文论专题课。根据我的听课笔记,程老师是2000年3月8日走上这门课的讲台的。他告诉我们,他的课是让大家细读苏联文艺理论家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他先讲两次,算是导读,接着是大家的自选动作:选取某章内容,细读一番,讲解出来。
说实在话,金的这本书我虽早已买到(购书日期是1993年12月),却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睡大觉。随着程老师的讲述,随着对话、庄谐体、狂欢化、复调小说、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等概念从他口中汩汩而出,我开始了对金的正式阅读。因为头一学期听过童老师的课,我对两位老师的讲课风格忍不住要暗中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如果说童老师主打慢条斯理,那么程老师则主打“大弦嘈嘈如急雨”,这种机关枪般的语速让我意识到,他不仅思维敏捷,而且还是个急性子。他要是唱歌,估计都会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节奏太慢,而是要换成“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的,为什么呢?因为《喀秋莎》是四二拍啊。
这就是我对程老师的最初印象。这种听觉效果,再加上那个精瘦、精干、精气神十足的视觉形象,更让我觉得程老师活力四射。实际上,那时他六十有三,已退休在家,却被大他一岁的童老师拉入彼时刚刚申报成功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成为退而不休的专职研究员,也成了童老师的左膀右臂。
线年春天,我不仅细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而且因为对第四章所论的“庄谐体”“梅尼普讽刺”“苏格拉底对话”兴趣颇浓,又决定把《拉伯雷研究》也读起来,因为尽管前书也谈到了狂欢式和狂欢化,却仿佛是即兴表演,我想弄清楚狂欢节、狂欢广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怎么回事,便无法在《拉伯雷研究》面前绕道而行,因为这本书中隐藏着这些问题的所有秘密。此书读毕,我特意在书后写了几句,记录彼时的激动之情,其中一句是:“读此书期间,受到的冲击与震动无与伦比。”也是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终于写出程老师这门课的课程论文《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金的狂欢化理论》,此文不仅受到程老师好评,而且发表也畅通无阻,甚至还获得了《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优秀论文奖。现在想来,假如没有程老师引导,我能顺藤摸瓜摸到《拉伯雷研究》吗?金能在我心目中占据一个永久而重要的位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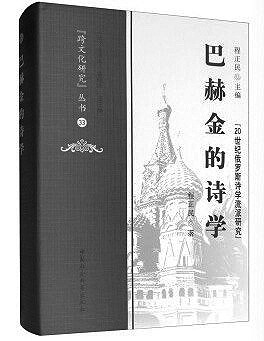
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书是让你长知识的,有些书则是能深入你的灵魂的。于我而言,《拉伯雷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然而,直到程老师去世的那天,我才从书架上取下他那本《金的诗学》,开始了对它的真正阅读z6尊龙凯时。因为我相信,在一个人辞世之后阅读其著作文章,才是对他最好的缅怀。因为这次阅读,我才意识到程老师简直就是文如其人:他的论述是质朴的,刚健的,冗繁削尽的,直来直去的,同时又是清晰的,谨严的,条分缕析的,举重若轻的。经过他的清理、反思、提炼和归纳,金的整体诗学就既琳琅满目,又井然有序了。这本书出版于2019年,是他晚年的著作。从字里行间,我仿佛也领略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风貌,精神不仅为之一震。更让我振奋的是,通过程老师的论述,我不仅复习了一遍金,而且还发现了金“艺术的内在社会性”与德国学者阿多诺“内在批评”之间的某种关联,同时,把它写成一篇论文的念头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
程老师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经说过:“在20世纪俄罗斯各种诗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也最令我神往的是金的诗学。”(《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这话我信。在我的心目中,程老师虽然写过《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等书,自然是俄苏文论研究专家,但这一专家的底色是金诗学。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金这碗酒垫底,他的俄苏文论研究是不是还能像现在这样丰满,或许就要打一个问号。
然而,直到程老师去世之后我才发现,他的金研究也正是起步于给我们这届学生上课的世纪之交,因为那正是他发表《金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的时候,也是钟敬文先生鼓励他将此文“扩展为一本书”的时候。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又有了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拓展之作《金的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当我意识到程老师是在“最美不过夕阳红”的季节才“咬定青山不放松”时,我对他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年届花甲意味着收官阶段的开始,程老师却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如此志在千里又如此壮心不已,怎能不让人敬佩?
连童老师都佩服不已!记得2013年12月26日,文艺学研究中心像往年一样,开了一个年终总结会。会开至最后,童老师说:“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学问,要坚持学术本位。你看咱们的程老师,他就一直研究金,研究来研究去,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你们要像程老师那样做学问。”
程老师的学问做得扎实,与他奉行“论从史出”有关,我就见他经常把这句线月上旬,中心在京郊大觉寺开务虚会,谈及学科发展,童老师强调,以后的文学理论建设不应该再是大兵团作战了,而是要每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琢磨多年,然后再与项目结合。轮到程老师发言,他则指出:“如何处理理论、历史和现状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论从史出很重要,但如果不重视现状研究,也很难往前走。像别林斯基、金这种理论家,其实都是非常关注文学现实问题的。”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自然首先关联着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但程老师之所以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要与现实相结合,显然与金脱不开干系。在《金的诗学》中,我就读到了这样的论述:“从广义上讲,论从史出,任何理论问题必须回归历史,通过历史研究阐明它的本质,阐明它的发展规律。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讲,文学史是要寻找文学的发展规律的,但规律不是凭空编造的,规律是要从历史的研究中得来的。”在另一处,程老师则直接指出:“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论从史出”的强调。由此我也意识到,虽然在晚年,童老师和程老师都讲文化诗学,虽然他们都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但程老师所谈论的文化诗学中多出了一个“论从史出”,这是来自金的馈赠。
由于程老师是金研究专家,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时常向他请益。记得2012年,我曾问他金是否用过“对话性杂语”(dialogic heteroglossia)。因为那时我正带着几位学生翻译美国学者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其中的术语需要拿捏准确。2017年,我向他请教哪种《金传》更值得一读,因为彼时我正在琢磨钱钟书的“暗思想”,想对钱钟书和金进行比较。2022年正月,我去给程老师拜年,当面问他“诗学”在俄语语境中有哪些解释,他马上取出一本《文学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翻到第196页,让我看作者哈利泽夫的说法。他还说:“我那本《金的诗学》不是送你了吗?我一开始就解释了诗学的三层含义,你回去可以看看。”我唯唯。
从程老师家出来,我忍不住感叹:程老师可真是一本活字典啊。与此同时,童老师的一个说法也在我耳边响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查记录,童老师的这番线日。那天下午,中心成员开会,童老师说他准备卸任,要把中心主任交给李春青教授。谈及中心的人员构成,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三老’‘五中’‘五青’。三老是我一位,程老师一位,李壮鹰老师一位。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这个大家庭现有‘三老’,那就是如有三宝了?”
实际上,那时才六十有四,称“老”似不合适,真正的老人只有童老师和程老师。他们都于1955年进入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又都来自福建,也都在大学期间崭露头角,最终成为留校人选。所不同者在于,童老师当时在中文一班,程老师在中文四班;童老师提前一年毕业,程老师则是完成四年学业后正常毕业,二人遂由同学变为同事,同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后来,童老师虽也被抽调到学校教务处干过,却基本上没离开过中文系,而从1965年起,程老师转入苏联文学研究所。直到1993年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程老师才重回中文系教书,在干过一届系主任(1995年—1997年)后,他就退休了。
据李春青教授回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程老师就成了童门心目中的“副导师”,原因在于,那时候童老师已请程老师帮忙做课题、带学生,等于是拉他入伙了(《我的“副导师”程正民先生》)。“苏文所”解散后,程老师何去何从,本来是有些犹豫的,因为他也可以选择去外语系,但童老师希望他“叶落归根”。在童老师的支持下,程老师不仅回到了中文系,后来还被推到系主任的位置。

线年代初期,童老师正准备厉兵秣马,大干一番。但那个时候,文艺学教研室青壮年居多,他们虽然朝气蓬勃,做学问是一把好手,但一旦进入行政管理、学科规划层面,或许就显得经验不足。于是,寻找一位知根知底的知心朋友来为他出谋划策、扬长避短,就显得迫在眉睫。这样,老同学程老师就成为最佳人选。因为他不仅谦和、低调、沉稳,而且脑子活,点子多,仿佛是“塔里点灯,层层孔明诸阁亮”。
记得在庆祝程老师八十华诞的会议(“俄罗斯诗学发展新趋势”学术研讨会)上,罗钢教授发言时把童、程二老师比作《红楼梦》里的钗黛关系,说他们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我则在致辞中借用苏联学者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说法,把童老师看作“主角”,把程老师视为“帮手”。我说:“在一个故事中,主角当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红娘的帮助,张生就娶不到崔莺莺;没有少剑波的参谋,杨子荣就打不进威虎山。可以说,在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中,正是他们这对老搭档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才完成了文艺学的学科叙事,把我们这个学科带向了一个辉煌时期。”
红娘是《西厢记》中的女二号,少剑波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参谋长,这两出戏许多人耳熟能详,是不需要解释的,需要解释的是普罗普的理论。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普洛普归纳出七种角色——加害者、赠予者、帮助者、公主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假冒主人公——它们涵盖了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围绕着每一种角色又构成了一个“行动圈”,它们在故事中行使着不同的功能。在北师大文艺学书写出来的故事中,童老师当然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公),程老师则是完美的帮手(帮助者)。他们要寻找的“公主”则是北师大文艺学的“顶层设计”,或者是童老师所说的,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在这种寻找中,程老师一直心甘情愿地当着帮手、配角、幕僚、绿叶,没有丝毫怨言。这种角色意识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彻头彻尾,心悦诚服,毫不含糊。
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童、程二人堪称完美的合作过程。我甚至觉得,不用“天作之合”来形容,就不足以表达这种完美度。
童老师去世之后,我开始担任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记得“新官”上任之后,我第一次到程老师家中拜访,他就讲起了自己当系主任的往事:“当时是学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然后就把我‘逼’上了系主任的位置。当了主任后,我去拜访了系里的几位老先生。因为当时中文系矛盾多,情况复杂,我就跟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诉苦,两位老先生谈笑间就给我出了主意、想了办法。其实钟老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像堂吉诃德;启老则像哈姆雷特,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世界就是由这两类人组成的。这不是我的观点,屠格涅夫早就写过文章。当了主任就得干事情,干事情就要惹人,但只要你是出于公心,又赢得了上面的支持,你就只管干下去。”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简明扼要,直指心窝,此谓程老师的谈话风格。他在那里现身说法,仿佛是手把手教我怎样当主任。
2017年6月14日晚上九点多,程老师给我打来电话。他开口就说:“今天是童老师走了两年的日子,真是快!我想他了,特意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会想到童老师,尤其是困难的时候?”我说:“是啊,因为我们既没有童老师的智慧,更没有他多年形成的那种威望。”于是程老师安慰我,说:“你也挺不容易的。以后遇事多商量,慢慢来,别着急。”实际上,我当主任期间,正是程老师意识到了我的“不容易”。虽然这些话显得抽象、缥缈,但毕竟也是一种安慰,仿佛在“晚来天欲雪”的时节来了一个“红泥小火炉”,让我感受到了融融暖意。
2018年10月20日,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文艺学新问题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在京举行,我请程老师致辞,他先是说了些面上的话,随后就转到我身上,说:“2011年在香山开会时赵勇刚买了辆新车,他开着车,把我和童老师送回了家。当时他是新手,车技一般,大家还不怎么敢坐他的车。七年之后他已是一个老司机了,坐他的车妥妥的。”程老师说罢,下面便是一片笑声和掌声。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2002年。20多年之后,答辩委员会其他委员的臧否之词大半都已忘却,但程老师的一个说法我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赵勇这篇论文能拎起来,不像有些同学写得比较散。他的论题是《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他提炼出了‘整合’与‘颠覆’这两套话语,这就拎起来了。”
按我理解,“能拎起来”就意味着论文有了核心命意。那个命意就仿佛一个抓手,可以放开,四面出击;能够归拢,万取一收。“拎不起来”的论文不一定就写得差,那里面也有散金碎玉,只是还没有炼成块,塑成形。究其因,要么可能是材料不过关,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我不敢说我的论文有多好,但好赖是有个抓手的;这个抓手是金镶玉还是铁家伙倒在其次。我能意识到这一点,全凭程老师的那次提醒,是他为我这篇论文的分量过了秤,命了名。他的说法尽管很朴素也很家常,没有“填补了……空白”之类的赞词,但我喜欢。后来,我之所以对一些诸如《萨特介入理论研究》《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有微词,提意见,便是因为这些题目只有论述范围,没有核心观点。用程老师的话说,就是“没有抓手,拎不起来”。若是用古文来说,最合意的句子应该是“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尽管程老师的论文批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后来在许多年里,我只是出了书奉上,请他雅正,并不敢随便写出什么文章就让他看。道理很简单,一是他年事已高,二是他手头的活儿也不少,我不能占用他的有限精力和宝贵时间。
然而,也是从童老师去世之后,我又开始让程老师审阅我的文章了。为什么我要让他受累?因为我在论文写作之余,也常常写一些涉及北师大人和事的文字,于是就有了让程老师看看的念头,因为他既可以指出写法好坏,也可以鉴别事实真伪,甚至还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细节材料。于是每每初稿既成,我便打印出来呈他审阅。通常三两天之后,程老师的“评审意见”就能到位。当然,我敢频繁打搅他,也是因为那些文字并非什么高头讲章,可以让他消愁破闷。尤其是后来得知程老师喜欢读这路文章之后,我就更是没有心理负担了。
现在想来,这些年我不断请程老师批作文、提意见,所图者何?应该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甚至也不图程老师的表扬。我大概觉得,每当写到北师大中文系传说中的人和事时,自己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资料,而程老师是现场目击者,我需要请他把关、验证,指点迷津。只有这样,我所回到的那个历史语境——亦即他与童老师都反复强调的那个东西——才不至于太抽象、太骨感,而是有了那么点血肉丰满的味道。程老师也恰恰心怀慈悲,肚里有料,于是他的评点常常恰到好处,他的建议往往切中肯綮。这种赐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后来甚至觉得,只有经他过目、被我再改之后,文章才拿得出手,否则,我心里就不踏实。
每每想到再也不能向程老师请益,我以后只能“文责自负”时,便不禁心中悲伤,有了一种“我有疑难可问谁”的荒凉。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程老师的离世,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师者、宽厚的长者,但于我而言,除此之外,还是一位热心而严谨的文章把关人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