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最近上网,想必看到不少这句话的身影。“草台班子”意味着世界潦草、荒谬、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既是戏谑,也是启发。
随后,层出不穷的世界出现了:“世界是一本巨大的霸总小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科目”“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世界的定义权,掌握在亲身经历它的人手中。
这个问题交给作家,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作家本人并未说过这个句式,以下回答均由编辑归纳。你还有哪些补充呢?欢迎留言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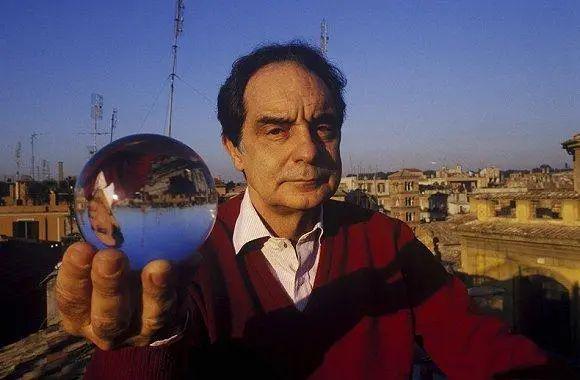
对于卡尔维诺来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城市,这一点在《马可瓦尔多》《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卡尔维诺笔下,走遍了世界各地的马可波罗提到城市就像是在描述梦境,城市里包含着所有的想象,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
“忽必烈汗发现马可·波罗的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仿佛完成那些城市之间的过渡并不需要旅行,而只需改变一下她们的组合元素。现在,每当马可描绘了一座城市,可汗就会自行从脑海出发,把城市一点一点拆开,再将碎片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
马可继续汇报他的旅行,但是皇帝已不再聆听,打断他说:“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描述城市,而你则说明是否真的存在我所想象的城市,她们是否跟我想象的一样。首先,我要讲的是一座台阶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常有热风吹过。现在,我再来讲讲她的一些奇景:一个像大教堂那么高的玻璃水池,供人们观看燕鱼游水和飞跃的姿态,并以此占卜凶吉;一棵棕榈树,风吹树叶,竟弹奏出竖琴之声;一座广场,环绕着马蹄形的大理石桌子,上面铺了大理石台布,摆着大理石制的食品和饮料。”
“她既无名称又无地点。我再向你说明一次描述她的缘故:在可以想象的城市的数目之中,那些元素组合缺乏联系的线索,缺乏内在的规律,缺乏一种透视感和一番故事的城市,必须排除在外。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
“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对于“镜子”这一意象的痴迷和恐惧几乎贯穿了博尔赫斯的创作,在他的文学宇宙里,世界是一个由镜子组成的迷宫,是虚无的增殖,是探索不尽的无穷幻影,是同一时刻下并行的无限空间。再老练的读者或许都难免迷失在这座镜子迷宫里,无声地看着镜面上浮现出自己愣怔茫然的脸。
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赖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人行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土,我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菲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自然史》初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仿佛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的空无一人的卧室,我看到阿尔克马尔一个房间里两面镜子之间的一个地球仪,互相反映,直至无穷,我看到鬃毛飞扬的马匹黎明时在里海海滩上奔驰,我看到一只手的纤巧的骨骼,看到一场战役的幸存者在寄明信片,我在米尔扎普尔的商店橱窗里看到一副西班牙纸牌,我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斜影,看到老虎、活塞、美洲野牛、浪潮和军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看到书桌抽屉里贝雅特丽齐写给卡洛斯·阿亨蒂诺的猥亵的、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的信(信上的字迹使我颤抖),我看到查卡里塔一座受到膜拜的纪念碑,我看到曾是美好的贝雅特丽齐怵目的遗骸,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的循环,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

宇宙(别人管它叫图书馆)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数目不能确定,也许是无限的,中间有巨大的通风井,回廊的护栏很矮。从任何一个六角形都可以看到上层和下层,没有尽头。回廊的格局一成不变。除了两个边之外,六角形的四边各有五个长书架,一共二十个,书架的高度和层高相等,稍稍高出一般图书馆员的身长。没有放书架的一边是一个小门厅,通向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六角形。门厅左右有两个小间。一个供人站着睡觉,另一供小便。边上的螺旋形楼梯上穷碧落,下通无底深渊。门厅里有一面镜子,忠实地复制表象。人们往往根据那面镜子推测图书馆并不是无限的(果真如此的话,虚幻的复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却幻想,那些磨光的表面是无限的表示和承诺……

金爱烂非常擅长描写在大城市生活的女性困境。虽然工作光鲜亮丽,但是出身普通,甚至贫穷的她们只能拼命抓住力所能及的资源,维持生活。“半地下”是韩国的一种住房形式,在金爱烂笔下,很多人都在半地下居住,这世界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半地下,人们在此艰难维生。
“妈妈决定在贴封条之前变卖值钱的物品。爸爸和我点头,努力寻找值钱的东西。不过十分钟,我们就发现家里能够卖上价钱的只有钢琴,而且也只能卖上80万。妈妈想了想,决定不卖钢琴。我摆摆手说,如果是因为我,那大可不必。我已经很久不弹琴了,而且真的没有任何留恋。钢琴上的玩偶睁着圆圆的眼睛。那都是爸爸从娃娃机里抓来的。经过深思熟虑,妈妈还是决定先把钢琴留下。
妈妈不可能不知道。我继续劝说妈妈卖掉钢琴。其实对我们来说,钢琴已经毫无用处了。妈妈好像把钢琴当成了某种纪念碑,说不定情况会好转呢,所以……说到这里就含糊了。最后我不得不带着钢琴去首尔。我离家那天,爸爸把摩托车的减震调到最大幅度,一边在路上飞驰一边哭泣。车速达到最快的时候,爸爸抬起前轮哽咽着说,孩子们,千万不要给人做担保!爸爸在塑料大棚旁边点头哈腰地被开了罚单。罚单如数送到在饺子馆干活的妈妈手里。
姐姐很不情愿的样子。趁着舅舅抽烟的工夫,我努力解释清楚。我以为妈妈都告诉姐姐了,没想到姐姐什么都不知道。姐姐郁闷地说:

我们坐在卡车前面,抬头看着钢琴。钢琴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自始至终保持着体面,优雅而淡定地站在那里。舅舅的卡车挡在路中间。我们急忙戴上棉手套。舅舅抓“住钢琴一角,我和姐姐抓住另一角。舅舅发出信号。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猛然抬起了钢琴。一九八〇年代产的钢琴在世纪末的城市上空短暂地飞翔。那个场面太美了。我几乎要赞叹出声。我们一步步挪动。双腿瑟瑟发抖,身体直冒冷汗。人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一辆轿车在后面鸣笛,似乎在催我们让路。不一会儿,住在二楼的房东穿着运动服走了下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圆滚滚的身材,看长相是那种按部就班做晨练的人。他站在门前哑然失色,似乎很难相信眼前的一幕。我托着钢琴,尴尬地点头微笑。姐姐也用眼神向男人问好。钢琴慢慢地把头探到又窄又陡的楼梯下面。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我们的尴尬又多了三分。突然,咣的一声!可能是舅舅没抓住,钢琴叽里咣当地滚下楼梯。我和姐姐急忙抓住钢琴的腿。在嗡嗡的共鸣中,发出多个时间在乐器里重叠的声音。钢琴上面的藤蔓图案在摇摆,像坏掉的弹簧。好像是撞掉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以为的浮雕其实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图案。我们看了看舅舅的脸色。舅舅做个手势,示意没关系,然后继续下楼。我并不担心舅舅受伤,也不担心钢琴的状态。相比之下,那个“咣——”的声音,回荡在我初到的城市里,这个真实、巨大而露骨的声音让我红了脸。”

并不是说波拉尼奥视世界为一场文学青年的集会,而是从阅读体验的角度出发,进入波拉尼奥的文学世界仿若误入街边某个不起眼的酒吧或咖啡厅,里面有一群乱糟糟的文学青年正围坐在一起争论诗歌,或是历史。
从《科幻精神》到《荒野侦探》到《护身符》再到《智利之夜》,波拉尼奥的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失意者,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和文字发生关联,尊龙人生就是博d88他们的美学主张和抱负都难以实现。 无人在意的青年诗人、靠微薄的薪水过活的文学评论家、三流报社的记者、以及在文哲系打杂工的墨西哥诗坛之母……他们在探寻中迷失,却依旧唱着一首关于勇气,和快乐的歌。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在很多人看来,接下来的几天,或者也许应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异常甜美的。在那之前我只是墨西哥城里的看客,一个自负的新人,二十一岁的蹩脚诗人。我必须说,这座城市不在意我,而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就只是卖弄学问和对文字的刻意雕琢。
他们个个苦恼,人人都是首都夜晚的忧郁青年。这些年轻的小伙带着自己折叠的手稿,用旧的书籍和肮脏的笔记本,在24小时开放的咖啡馆或者世界上最压抑的酒吧里落座。我是那里惟一的女性,有时我是丽莲·瑟尔帕斯的幽灵(关于丽莲,后面我还会说到)。这些年轻人给我朗读他们的长诗、短诗以及绕口的译文。我拿起那些稿子,背靠餐桌,默默地阅读。那些年轻人围着餐桌在干杯,都焦急地装出有才智或者能讽刺或者愤世嫉俗的样子,这些可怜的天使啊,我专心致志地看那些辞藻(我本喜欢说语言流畅,可是它们并非如此,那里面没有什么流畅的语言,只有结结巴巴的单词)并且深入其中。片刻间,我独自面对那些被年轻人的忧伤和青春闪光弄得磕磕巴巴的词汇;我独自面对那些破镜子的碎片;我张望着,确切地说是寻找那些廉价的水银。我看见了自己!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 — 1938)身高六英尺半(近两米),体重约两百五十磅,他习惯站在冰箱前,拿冰箱顶当桌子写作。或许正因为身材魁梧,沃尔夫胃口巨大,感受力又极强,有力量唤起并召回与各种东西相关的感觉,并将之具体描绘出来。
沃尔夫的巨大胃口不仅仅是针对食物——在那种想知道一切的巨人性“饥渴”中,他写出了《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
在短篇《十月啤酒节》中,沃尔夫同样描绘了这样一种“强烈的饥饿感”,并直陈:“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胃。”
我们又去了另外几家大型啤酒厂的大厅,但都无功而返。最后,我们在大厅门口发现了一个啤酒摊,几张桌子摆在一个石子空地上,一道栅栏将拥挤的人流隔在了外面。几张桌子上坐了一些人,但是大多数位子都空着。天色渐暗,空气开始变冷,传来阵阵寒意。人们发疯似的渴望进入那个大厅,渴望进入那个温暖、人声鼎沸、醉意浓浓的环境里。但是起初的兴奋、拥挤的人群,以及人们的谈话声、缤纷的色彩和激动的情绪开始让我们觉得有些疲惫了。“我们坐在这儿吧。”我指着大厅门口的一张空桌子说道。海因里希凑在一扇窗户前,不安地瞅着大厅里烟雾缭绕的混乱情形,模糊的人影像幽灵一样互相拥挤,推推搡搡,迷失在烟雾和瓦尔哈拉殿堂的瘴气中,然后就同意了我的提议,挑了一个位子坐下,但却难掩内心的失望。
“那里面很不错,”他说,“不应该错过的。”这时,一位村妇来到了他们身边,每只结实的手里都颤颤巍巍地端着六大杯泛着泡沫的烈性十月啤酒,她十分友好地冲他们一笑,问道:“要淡啤酒还是黑啤酒?”他们齐声说道:“黑啤。”话音未落,她就已经把两大杯泛着泡沫的啤酒摆在了我们面前,然后走开了。

“啤酒?”我问,“为什么要喝啤酒?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喝啤酒?慕尼黑以啤酒闻名,城里还有成百上千家啤酒馆,为什么啤酒厂还要在这里搭建如此巨大的棚子?”
“是啊,”海因里希回答,“不过,”他笑了一下,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这是十月啤酒,烈性是平常的两倍。”
然后我们举起巨大的酒杯,笑着说“干杯”,我们的杯子碰到了一起。在那个寒意料峭的天气里,深深地喝进一大口浓烈、清爽的啤酒,我们的血管顿时充满了力量。我们周围的人们都在大吃大喝,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一些穿着盛装的农民要来了啤酒,解开了随身带来的几个包裹,把丰富的食物摆在桌子上,开始大吃大喝起来。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壮汉穿着白色的毛袜,包住了健硕的小腿,但却把膝盖和脚裸露在外。他从包裹里取出一把大刀,砍掉了咸鱼的头,咸鱼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美丽、金色的光芒。
每个人都在大吃大喝。一种强烈的饥饿感——贪婪、不知餍足的饥饿感——恨不得吞下世界上所有的烤牛肉、所有的香肠、所有的咸鱼——向我袭来,将他紧紧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食物——令人开心的食物,只有啤酒——十月的啤酒。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胃——崇高的天堂就是食欲的天堂,精神的痛苦在此刻烟消云散。这些人对书籍了解多少?对艺术懂多少?对灵魂的喧闹、精神的冲突和痛苦了解多少?对希望、恐惧、仇恨、失败、抱负,以及狂热的现代生活了解多少?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

辛格并未直接详细地描写过屠宰场,但笔下却常常出现屠宰场这一要素,如市场、屠夫、屠宰礼拜师、在屠宰场工作的小伙子以及拔鸡毛的母亲等。辛格也常常写到动物,对他来说,动物与苦难与人的苦难一样值得悲悯,市场上被宰杀的千百家禽与、德国对犹太人的同样恐怖惊心。正因为如此,世界和屠宰场别无二致。
正如辛格自己所说:“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屠场,一个庞大的地狱。……世界上有这么许多苦难,唯一的补偿是生活中小小的欢乐、小小的悬念。”

今天,我对一切都要作出决断,雅夏在敞篷四轮马车里对他自己说。今天是我的最后审判日。他闭上眼,一心一意地盘算起来。但是他经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一个主意也决定不了。尽管他眼睛不看,他又听到这个城市的声音,用到它的气味。赶大车的直吆喝,鞭子甩得啪啪响,孩子们高兴地乱嚷乱叫。从院子里和集市上微风暖洋洋地吹来,带来了扑鼻的粪便味、炸洋葱味、污水味和屠宰场的血腥味。工人们在拆木板人行道,把鹅卵石换成方石,装煤气街灯,开沟铺设下水道和电话线。城市的内脏在重新安排。有时候,雅夏睁开眼来,他觉得敞篷四轮马车快要陷进沙坑了。大地看上去好像快要崩溃了,建筑物摇摇欲坠;整个华沙呈现出将要遭受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同样命运的面貌。他现在怎么能决定任何事情呢?敞篷四轮马车驶过格诺那街上的会堂。我什么时候上那儿去过?他问他自己,脑子里一片泥乱。是今天吗?还是昨天呢?两天并成一天了。他当时披着祈祷巾,戴着祈祷盒在那里祈祷,心里充满着虔诚,现在他感到恍如隔世,像做梦似的。什么力量附在我的身上。我的精力已经完全垮啦!敞篷四轮马车驶到埃米莉亚家门口;雅夏递给赶车的一个盾,不是平时的二十个子儿。赶车的把找头给他,但是雅夏挥挥手。他是个穷人,雅夏想,让他多拿十个子儿吧。每一件好事都会提高天上的地位。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家族,所以——不要内战,不要,不要自我封闭,不要让彼此的历史消逝于时间。正如《百年孤独》的末尾所写:
奥雷⾥亚诺平⽣从未像此刻⼀般清醒,他忘却了家中的死者,忘却了死者的痛苦,⽤费尔南达留下的⼗字⽊条再次钉死门窗,远离世间⼀切⼲扰,因为他知道梅尔基亚德斯的⽺⽪卷上记载着⾃⼰的命运。他发现史前的植物、湿⽓蒸腾的⽔洼、发光的昆⾍⺒将房间内⼀切⼈类踪迹消除净尽,但⽺⽪卷仍安热⽆恙。他顾不得拿到光亮处,就站在原地,仿佛那是⽤卡斯蒂利亚语写就,仿佛他正站在正午明亮的光线下阅读,开始毫不费⼒地⼤声破译。那是他家族的历史,连最琐碎的细节也⽆⼀遗漏,百年前由梅尔基亚德斯预先写出。他以⾃⼰的⺟语梵⽂书写,偶数⾏套⽤奥古斯都⼤帝的私⼈密码,奇数⾏择取斯巴达的军⽤密码。⽽最后⼀道防线,奥雷⾥亚诺在迷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时就已隐隐猜到,那便是梅尔基亚德斯并未按照世⼈的惯常时间来叙述,⽽是将⼀个世纪的⽇常琐碎集中在⼀起,令所有事件在同⼀瞬间发⽣。奥雷⾥亚诺为这⼀发现激动不已,逐字逐句⾼声朗读教皇谕令般的诗⾏,当年阿尔卡蒂奥曾从梅尔基亚德斯⼝中听闻,却不知道那是关于⾃⼰死亡的预告。他读到⽺⽪卷中预⾔世上最美的⼥⼈的诞⽣,她的灵魂与⾁⾝正⼀起向天⻜升;他读到那对遗腹孪⽣⼦的来历,他们放弃破译⽺⽪卷不仅因为缺乏才能和毅⼒,更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读到这⾥,奥雷⾥亚诺急于知道⾃⼰的⾝世,跳过⼏⻚。此时微⻛初起,⻛中充盈着过往的群声嘁喳,旧⽇天竺葵的呢喃窸窣,⽆法排遣的怀念来临之前的失望叹息。他对此毫⽆察觉,因为他发现了关于⾃⼰⾝世的初步线索。他读到⼀位好⾊的祖⽗⼀时迷了⼼窍穿越幻象丛⽣的荒野,寻找⼀个不会令他幸福的美⼥。奥雷⾥亚诺认出了他,沿着亲缘的隐秘⼩径追寻下去,找到了⾃⼰被赋予⽣命的⼀刻,那是在⼀间昏暗的浴室⾥,蝎⼦和⻩蝴蝶的环绕间,⼀个⼯匠在⼀个因反叛家庭⽽委⾝于他的少⼥⾝上满⾜了。他读得如此⼊神,仍未发觉⻛势⼜起,飓⻛刮落了门窗,掀掉了东⾯⻓廊的屋顶,拔出了房屋的地基。到这时,他才发现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不是他的姐妹,⽽是他的姨妈,⽽当年弗朗⻄斯·德雷克袭击⾥奥阿查不过是为了促成他们俩在繁复错综的⾎脉迷宫中彼此寻找,直到孕育出那个注定要终结整个家族的神话般的⽣物。当⻢孔多在《圣经》所载那种⻰卷⻛的怒号中化作可怕的⽡砾与尘埃旋涡时,奥雷⾥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跳过⼗⼀⻚,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刻,译出的内容恰是他当下的经历,预⾔他正在破解⽺⽪卷的最后⼀⻚,宛如他正在会⾔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死亡的⽇期和情形,但没等看到最后⼀⾏便已明⽩⾃⼰不会再⾛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亚诺·巴⽐伦全部译出⽺⽪卷之时被飓⻛抹去,从世⼈记忆中根除,⽺⽪卷上所载⼀切⾃永远⾄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次机会在⼤地上出现。


灯塔是光明,是指引,灯塔所在就是陆岸所在。在一个人人有彼岸,人人都渴望“上岸”的时代,世界仿佛也具象化成一座巨大的灯塔,正如作家伍尔夫所写:
“他⼀定已经到了。”莉莉·布⾥斯科⼤声说,突然感到⼼⼒交瘁。因为那座灯塔已经⼏乎看不⻅了,隐没进⼀⽚蓝⾊的雾霭之中。她⼀边努⼒地看着灯塔,⼀边努⼒想象他在那⼉上岸的情景——⼆者似乎是⼀体的,是同⼀种努⼒——把她的⾝体和精神抻到了极限。啊,但她松了⼝⽓。不管那天早上他离开之际她想要给他什么,她终于都给他了。
“他上岸了,”她⼤声说,“终于了结了。”之后,⽼卡迈克尔先⽣猛地⽴起⾝,站在她的⾝旁,微微喘着粗⽓,像⼀位苍⽼的异教神祗,⽑发浓密杂乱,头发上粘着⽔草,⼿⾥握着三叉戟(那不过是⼀部法国⼩说)。他与她并肩站在草坪边缘,他壮硕的⾝躯微微摇晃,抬起⼀只⼿,搁在眼睛上⽅遮阳,说道:“他们就要上岸了。”她觉得她⼀直以来的感觉没错。他们⽆需交谈。他们⼀直在想同样的事情,⽽她什么也没问,他就回答了她的问题。他站在那⼉,仿佛正在伸开双⼿,遮住⼈类所有的软弱和痛苦;她觉着他正在宽容⽽悲悯地审视着他们最后的归宿。随着他的⼿缓缓落下,她想,现在他已让这⼀幕结束,她仿佛看⻅他任凭⼀只由紫罗兰和⻓春花编织的花环从他的头顶落下,飘飘摇摇,最终落到了地上。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2018)剧照,讲述维伍尔夫与薇塔·萨克维尔·维斯特之间爱情与友谊的故事
她仿佛受到了那边什么东⻄的召唤,急忙转向她的画布。它就在眼前——她的画。是的,它所有的绿与蓝,它恣意纵横的线条,它对什么东⻄的企图。她想,它会被挂在阁楼上;它会被毁坏。可那⼜有什么关系呢?她重新提起画笔,⾃问道。她看向台阶;空落落的;她看向画布;模糊不清。她的内⼼泛起⼀阵突如其来的强烈悸动,仿佛在那⼀瞬间看清了它,她在画布的中央添了⼀笔。完成了;画好了。是的,疲惫不堪地放下画笔,她想:我终于画出了我曾⻅到的景象。

李娟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牧场 ‘ 天空占四分之三,大地占四分之一 ’ 。这样的世界通达无碍,风一起,就跟着倾斜。世间所有生灵天生地长,自由自在,置身于阿勒泰的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或许才能真正感叹一句:“人生是旷野。”
而此刻,我仍生活在偏远寂静的阿克哈拉村,四面茫茫荒野,天地洁白——阴天里,世界的白是纯然深厚的白;晴天,则成了泛着荧荧蓝光的白。这几天,温度一直降到了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大雪堵住了窗户,房间阴暗。家中只有我一人。天晴无风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通向院门。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然而挖了两三米就没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我们走的路是戈壁滩上的土路(——真丢人,我叔没执照,车也没牌照,不敢骑上公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细而微弱的路的痕迹,在野地中颠簸起伏。这条路似乎已经被废弃了,我们在这样的路上走过好几个小时都很难遇见另一辆车。大地辽远,动荡不已。天空更为广阔——整个世界,天空占四分之三,大地占四分之一尊龙人生就是博d88。

而风起的时候,又总让人觉得世界其实本来如此——世界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大风。我在半山腰往下看,再抬头往高处看。我看到全世界都是一场透明的倾斜,全世界都在倾向风去的方向。我的头发也往那边飘扬,我的心在原地挣扎,也充满了想要过去的渴望。
森林朝那边起伏,河朝那边流。还可以想象到森林里的每一棵枝子、每一根针叶都朝着那边指;河里的每一尾鱼,都头朝那边,在激流中深深地静止。
我总是会在有风的时候想没风时候的情景——天上的云一缕一缕的,是飘动的。而此时,那云却是一道一道的,流逝一般飞快地移动。

许子东曾评价王朔,说他“王朔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说话像开了水龙头,拦也拦不住。”在王朔的眼中,万事万物皆可调侃,知识分子、作家,甚至连王朔自己,都逃不过王朔的嘴。这种无畏冒犯的精神,倒是像极了当下流行的脱口秀。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脱口秀舞台,那王朔一定能在上面大放光彩,毕竟整个世界在他眼中,也许就是一个 巨大的段子 。
中国读书人也有这么一个信仰,孩子就是他们留下的头发、牙齿和粪便,当然他们不这么叫,叫“读书种子”。有孩子在,不肯死或不甘心死的读书人就觉得留了一点东西给后人,就觉得自己没全死而快乐了。和伟大的人搞惯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自己也很伟大,或者他老大,我老二。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哪句不是自己的。其实这很容易分辨——哪句也不是你的。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
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你不能说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英语,但丁发明了意大利语,他们充其量是一个整理者,第一个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借此而扬名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王朔及其作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开始,哗众取宠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须采取的姿态,连累得其他很多老实本分的作家也跟着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大家对他的愤怒,瞧不起他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王朔才能证明我们的文学是繁荣的,百花齐放的。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3.《阿莱夫》,原题《阿莱夫》,[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王永年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06
4.《虚构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杜撰集》,原题《通天图书馆》,[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王永年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05-01
6.《科幻精神》,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侯健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03-01
8.《上帝的孤独者》,原题《十月啤酒节》,托马斯·沃尔夫 著,刘积源等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05
10.《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范晔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新经典文化,2011-06

